
「可以說,這些經歷讓我心靈變得強壯,有更強的同理心。我會覺得,當別人說自己有困難的時候,你不要批評人家為何不解決自己的困難,他背後可能有許多原因,是你不理解的。」施婉萍 (Felix)教授歸結出,自己對弱勢社群包括聾人身心權益的關心,或許跟自己不一樣的成長背景有關。
星期四下午,我們來到「遺世獨立」的中大教研樓二座(近科學園 ),穿過婆娑樹影,走入大片草地前的白色大樓,Felix的辦公室──中大手語及聾人研究中心就在其中。

中大手語及聾人研究中心的所在大樓。(圖:ORKTS/CUHK)
由英國文學走向聾人研究
Felix是中大語言學及現代語言系副教授,亦是手語及聾人研究中心的聯合主任。上年她跟心理學系的麥穎思教授合作,透過中大知識轉移項目基金(KPF),展開聾人精神健康社區計劃,包括建立具備手語雙語的心理健康資料庫,讓聾人理解「抑鬱」或「焦慮」等心理徵狀;透過故事工作坊,提升聾人的身份認同和精神健康。
作為健聽人士,也沒有聾人親友,究竟Felix如何走上聾人和手語研究的學術之路?故事要從大學本科說起。
她是中大校友,90年代以「暫取生」(拔尖)計劃獲錄取入讀英文系。她坦言對修讀英國文學不太投入,「讀得有些辛苦」,反而語言學讀得津津有味,「學習語言學的過程中,譲我明白到,如果有些書會讀到打瞌睡,就證明不適合自己;相反,如果越讀越精神,那就是自己的興趣所在了。」她打趣道。
本科畢業後,她沒有接受母校校長的邀請返回母校當英文老師,選擇繼續攻讀語言學碩士,她本來是研究幼童學習廣東話的現象,後來因為論文指導老師離開了中大,她有了轉題目的契機。
「那時我正好是Gladys(鄧慧蘭教授)的教學助理,她問我有沒興趣研究手語,我很快就答應了。」她自言,自己對於人生方向,多是順水推舟,「從來不會說我一定要做這做那,反而順着自己的興趣,機會到了就會嘗試。」
她直言,攻讀碩士時才開始接觸聾人社群,當初出發點絕對不是甚麼偉大的使命感,反而是手語純粹的吸引力。
「那時看書和文獻,關於手語的Brain Science同Grammar分析,覺得好有趣,是一門新的學問,手語跟廣東話和英語不一樣,原來聾人的世界是這樣看語言的,真是大開眼界。98年我開始學習基本的手語,真的由一二三四;ABCD;爸爸媽媽這些單詞學起。」
關於Felix找「名師」教手語的奇遇,我們早在鄧慧蘭教授口中聽聞過。她說過,當年研究中心第一位聾人研究員、罕有以手語為母語的朱君毅( Kenny),就是「Felix在街頭找回來的」。
Felix為故事解畫。

Felix(右)曾是鄧慧蘭教授(中)的學生,今日兩人成為合作無間的同事,是推動手語及聾人研究中心工作的重要推手。(圖:ISO/CUHK)
膽粗粗街頭找手語老師
「我讀碩士才開始學手語,第一位老師是弱聽的,他手語純熟,是一名 late learner, 後來看得越來越多文獻,知道最好都是要跟 native signer學習一段時間,正如你學習其他外語一樣,於是我就展開了尋找native signer的旅程。有一日我去男朋友(後來的丈夫)家,夜晚離開的時侯在巴士站見到一對情侶在打手語,我就放棄登上已到站的巴士,膽粗粗上前問對方可否教我手語。」
她形容自己當時有一股傻勁,就這樣交換了聯絡方法,沒想到對方原來真的來自聾人家庭,是不折不扣的native signer。之後不時上那位女生的家學手語,還認識了女生同為聾人的弟弟,即後來成為研究中心員工的Kenny。而Kenny亦由當日的地盤工人,經過多年的苦讀,不但完成中大學位,現正繼續攻讀碩士,還成為中大的手語老師,人生軌跡完全逆轉。
「我的手語程度有幾個 big jumps,其中一個就是經常跟Kenny去吃午飯,我教他英語,他會指正我的手語。語言就是這樣學回來的,只要多跟聾人做朋友,一定會有進步。」
她說,讀碩士是隨性的決定,讀博士卻是意志堅定得多。在三年碩士課程中,她目睹當年教育局官員對手語的誤解實在「難以撼動」(以往手語教育不被重視,聾人往往只能佩戴助聽器或讀唇),「明明手語幫到聾童學習和發展,但官員不理解,偏偏他們是制定政策的人。我覺得我要在學術上裝備自己,才可以改變體制。」
經過深思熟慮,她於2000年前往英國布里斯托大學攻讀聾人研究博士學位。她形容這次升學「決心好大」,因為她是先獲得劍橋大學取錄修讀英語第二語言相關的研究院課程,但她放棄了劍橋的入學邀請,毫不猶豫走向聾人研究的方向。
如此取捨,外人或難以理解,畢竟劍橋是舉世知名的學府,家人有否微言?
「沒有,我從小父母都忙於爲口奔馳,所以給我好多自由的空間,對我的決定沒有甚麼質疑。」她進一步分享不一樣的成長背景,如何成就今日心理健壯的自己。

Felix樂意分享自己的經歷,鼓勵學生在選擇人生方向時,保持開放的心。(圖:ORKTS/CUHK)
走難經歷助變得硬淨
「你看我英文名串法(SZE Yim Binh)有點奇怪,其實我是越南華僑,在越南出世,我在1976年兩歲的時候,我們一家人才來香港。我爺爺本來很富有,在胡志明市的唐人區做水果生意,外號蕉王。1975年北越軍隊佔領南越,正式統一越南,並開始大舉排華,廢掉原有貨幣,沒收華人資產,限制華人自由,爺爺跟其他富有的華人一樣,傾間盡失家財。」
1970中開始,大量越南船民湧入香港,幸運的是,Felix的爸爸因爲年少時曾到香港留學,取得香港身分證,他們一家獲英殖政府包機接載回港,「當時絕大部分的華人要坐船偷渡離開,冒極大的風險,我阿姨和她男朋友的一家十幾口就這樣葬身大海。」她形容那段越南華僑被逼害、冒死逃難的歲月「慘絕人寰」。
「有不少華人家庭一夜之間所有金錢化為烏有,無法忍受越共的逼害,選擇在飯菜中落老鼠藥,一家大細一起自殺,聽到這些事,覺得好震撼。」她兩歲就來香港,記憶不深,這些悲劇都是後來從爸爸媽媽口中得知。
越南難民議題一度困擾香港達25年,社會不乏歧視聲音。Felix在高小初中時期,亦曾因為越南華僑這身份遭受同學言語騷擾,「騷擾維持了一段短時期,後來可能因為我讀書成績不錯,他們不敢再欺負我。這些經歷或多或少令我心靈強壯起來, 學習面對別人的嘲笑,不會放在心上。可能因爲我這個難民的背景,當我接觸弱勢社群時會有較強的同理心。」

乘搭交通工具等日常事,對於聾人而言亦可以是壓力源頭。(圖:ORKTS/CUHK)
聾人心理健康受忽視
這份同理心亦某程度上造就了這個聾人精神健康項目的出現,「在英國讀博士的時候,一位有心理學背景的同學曾經分享,一般健聽人覺得不會有壓力的情況,對聾人而言可能壓力是非常大的,不加留意就會忽略他們的需要。」
「例如當時在英國乘搭巴士,乘客上巴士時要告訴司機目的地是甚麼,司機才告之該付的車資,然而聾人不容易做到,與此同時後面有其他人排隊等上車,司機如果顯得不耐煩,聾人乘客會感到焦慮和壓力。而在一些精神健康問卷,因為問卷的設計問題,令人不理解為何聾人坐巴士都感到壓力,容易因此誤會他們有嚴重的焦慮,而誤判他們有精神病,形成惡性循環。」
她指出,聾人面對上述雙重不理解,若果心理醫生欠缺有關訓練,只會以藥物解決,轉介他們去看精神科醫生,而不是通過理解和解決他們實際的需要。
另一件事令她十分感觸的,是2008年的「李菁事件」。李菁被譽為聾人狀元,然而大學畢業後一直找不到工作,後來獲介紹來中大手語及聾人研究中心工作,「她自小在一個全口語的主流學校成長,面對相當大的壓力,加入我們中心前精神狀態已不太好,來到中心後她有努力融入打手語的聾人世界,可能在過程中免不了會感到挫敗吧。」她哽咽道出。
「她的離開,對我們中心的一眾同事來說是沉重的打擊。這件事令我深深體會到聾人精神健康的重要性,不希望同類事件再發生。」感召背後,Felix強調年輕同事的推動亦十分重要,包括即將修讀輔導碩士課程的劉紫蕾(Kloris),和現正攻讀臨床心理學碩士的朱憫謙(Ham)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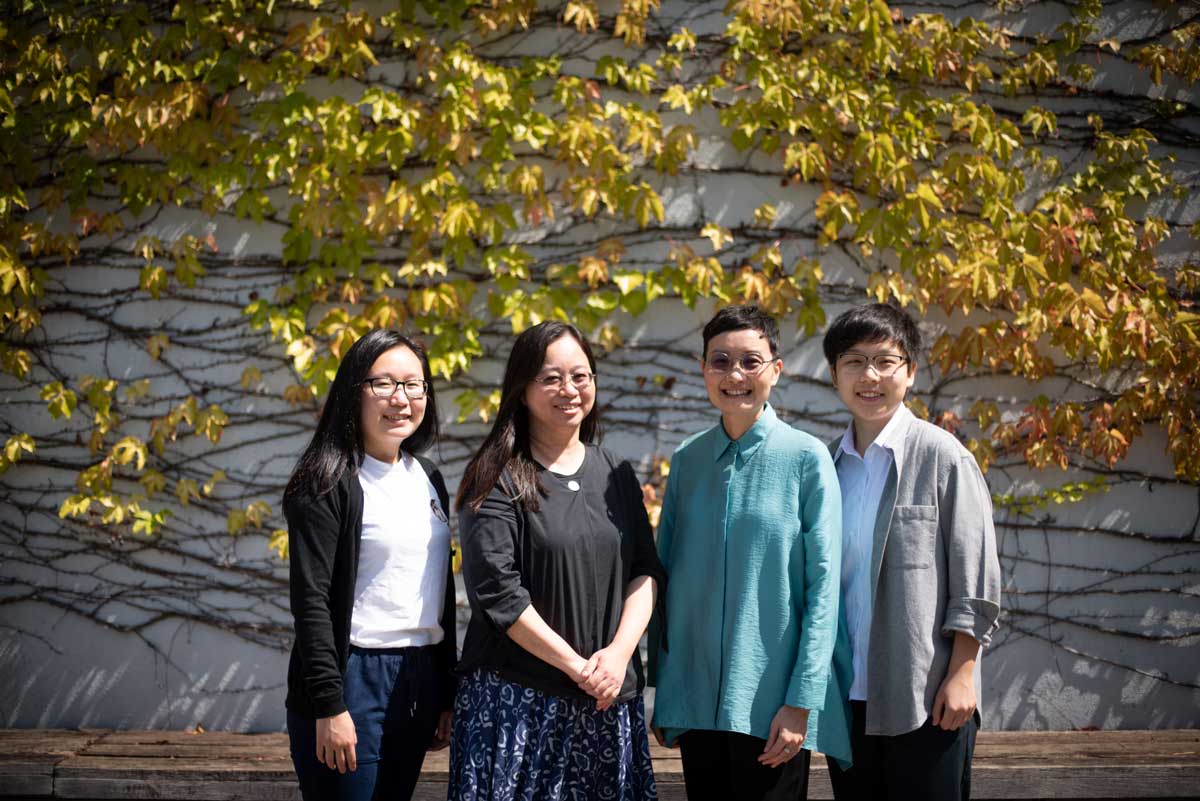
聾人精神健康社區計劃成員,施婉萍教授(左二)、麥穎思教授(右二),以及兩位得力助手 Kloris(左一)和Ham(右一)。(圖:ORKTS/CUHK)
這個項目亦反映了2003年成立的研究中心裏面,幾代師生的傳承。
28歲、健聽的Ham在中大讀心理學本科時,無心插柳下上了Kenny(中心第一位聾人同事)教授的手語班,感到眼界大開,自此不斷進修,成功當上手語傳譯員。她立志成為一位能夠用香港手語,向聾人提供心理治療的臨床心理學家。跟Ham食過一頓飯,聽她慢條斯理道出這份偶然產生的熱情源起,令人大感佩服。
項目結合中大語言學系和心理學系的學術知識和經驗,Felix和Kloris負責將心理學概念用手語拆解,以建立一個相關的手語資料庫。Ham和麥穎思教授團隊則會提供一些說故事的工作坊,增加聾人與社區的接觸,一方面讓聾人「發聲」,「打」出自己的故事,另一方面提升大眾的意識。
分享完一些香港手語和聾人文化的小知識後,Felix揹起書包急急腳離開,「我要到獸醫診所接回我隻竉物天竺鼠。」
眨眼斷句|學人關鍵字

(圖:Unsplash)
Felix提到,聾人及手語研究的範疇廣泛,「有趣的課題我都會研究」,包括亞洲手語如何婉轉表達性相關的概念;有多少健聽人的手勢(Gesture)被手語正式採用;學習手語會否幫助長者改善認知和空間辨別的能力等等。
面部表情、身體擺動、眼神是聾人溝通重要的一環,「眼神好重要,一break eye contact,代表他們想disengage,所以聾人鬧交,擰轉面就得架喇。」「在句子之間,他們還會用眨眼來斷句,我發表過相關研究,結果好有趣,但分析大量眨眼數據的過程好痛苦。」她苦笑道。



